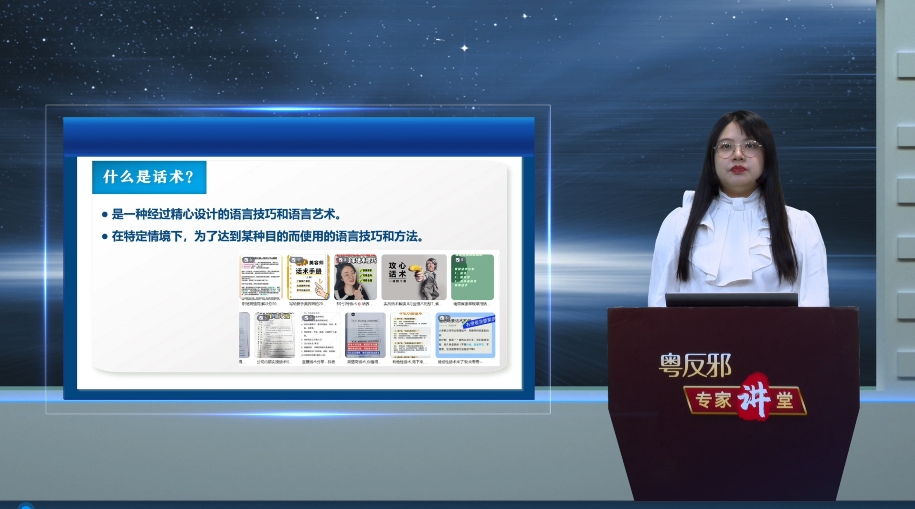浅论我国依法治理邪教问题的法律实践

邪教摧残人的身心,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人类文明,是世界公害、社会毒瘤。邪教问题是各国政府都必须严肃对待的社会问题,运用法律手段预防和惩治邪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2019年是我国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20年,20年来,党和政府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法律实践,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渐成体系,覆盖面广,反邪教立法涵盖了维护国家安全、群众利益和社会安定等各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已逐步形成了相对健全的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法律体系,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邪教问题制定的单行法律,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邮政法等专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国务院制定的《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等国务院部门规章,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到守护群众安全等各方面均有了明文规定,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邪教法律体系,为取缔打击邪教组织、遏制邪教活动提供了较充足的法律依据。
其中,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邪教犯罪处置做出了修改和完善,根据宽严相济的原则对邪教牟利型犯罪和组织型犯罪等不同情况明确了不同量刑标准。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司法解释中对邪教的定义做过界定,2017年2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为各级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门识别、鉴定邪教组织提供了更有效的判别依据。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新时代政法工作进行全面制度擘画,规定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指导政法单位和相关部门做好反邪教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工作。这些法律的制订、修改使我国反邪教立法工作进一步涵盖了从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方方面面,完善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理邪教问题的法治思想。
二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体现了法律实践与社会道德、文化和理想价值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认定的邪教组织有24种,其中,冒用佛教及气功名义的有6种,冒用基督教名义的有18种。我国反邪教工作主要从1995年开始,反邪教专门立法主要从1997年开始,由于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早期对邪教组织的认定主要依靠国家政策、部门规章等,如1995年11月中办、国办认定7种邪教:“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观音法门”、“主神教”,1999年国家认定1种邪教:“法轮功”;2000年4月公安部认定14种邪教:“被立王”、“统一教”、“三班仆人派”、“灵仙真佛宗”、“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常受教”、“能力主”、“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实际神”,“华南教会”、“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圆顿法门”。
近年来,随着反邪教立法的完善,对邪教组织的认定主要由法院进行。如2014年10月,山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全能神”组织系冒用基督教名义,曲解《圣经》内容,编造歪理邪说,神化首要分子,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邪教组织”的特征,应当依法认定为邪教组织;2015年7月,广西南宁市某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银河联邦”为邪教组织。法院认为,郑辉冒用佛教的名义,通过组织非法“法会”,制作、印刷、散布非法出版物、宣传品的形式,散布迷信邪说,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众多信徒,形成危害社会的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构成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2015年10月,广东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吴泽衡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七百一十五万元。同时认定,“华藏宗门”(又称“华藏心法”、“华藏玄门”、“华藏法门”)为邪教组织。这些判例表明我国依法治理邪教的法律实践已逐步完善。
然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伙同邪教组织骨干,罔顾邪教祸国殃民的事实,紧咬“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教条,处心积虑地攻击我国政府依法打击、取缔邪教组织的法律实践,对我国早期打击取缔邪教的正义行为予以诟病。事实上,这些诟病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当今西方法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罗纳德·德沃金[美]认为,一般而言,法官在判案时最常用到的是规则,即法的确定性层面;当法官面临棘手案件时,可能会找不到能适用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得不求助于非规则标准,即援用原则、政策及惯例等不甚具体的标准,即法的不确定性层面。法律离不开人们的道德、文化和理想等因素,法官在从事建构性解释法律的时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所作出的解释必须恰如其分地“适合”整个法律制度的要求;二是这种解释必须反映出该法律制度道德价值的最佳状态。法的变化乃是由于法的非规则标准发生了变化,而规则本身并未发生变化,即是说法的内涵中有一部分是变量,而另一部分则是常数。这种解答既表明法是确定的,也指出了它的不确定性,既维护了法的自主性,也揭示了法的灵活性。法相对自主的观点已为很多不同流派的学者所接受。比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和生命。它既独立于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再如,尼古拉·卢曼在其法社会学理论中也提倡一种相对自主的法律观。[1]由此可见,法律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系统,反邪教斗争由于其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立法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反邪教法律实践必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早期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规定,我国政府在处置“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实践中只能根据邪教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社会公共秩序等现实危害,由相关部门按章进行认定、打击和取缔,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三是直面风险,防患未然,承担起法律制度在揭示、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社会责任
邪教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邪教对社会的破坏,更加深层次地体现为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动摇国家正常的社会教化功能。历史上,出于统治需要,对于邪教类活动,即使没有起义、反叛等重大危害活动,聚众和敛财本身就是危及社会统治的重大不安因素,任何统治阶层对此都不会等闲视之。将邪教类活动扼杀在萌芽阶段,是处理邪教案件的最佳方式。明朝,朱元璋公开立法禁止包括明教在内的各种异端信仰,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明清时期,以白莲教为主的各种邪教,有的也只是“聚从敛钱”,并无谋反之意,但因为聚众民众,极易受邪教煽惑,所以不管有没有谋反的实际行为,都列入危及政权的重要行为,被严厉打击。[2]爱国诗人陆游对此也曾有深刻论述:
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劫掠,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唯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接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危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名号不已,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万一窃发,可以寒心。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渭南文集》卷五所载《条对状》)
可见,邪教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有着巨大的区别,反邪教法律实践需要有更大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中,随着犯罪组织的被摧毁,犯罪行为被依法惩处,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对该具体犯罪所造成的危害性的消除。在邪教犯罪案件中,由于受害人的思想被邪教组织深度蛊惑、受害人的精神被严格控制,犯罪后果不会因为犯罪组织的被摧毁、犯罪行为的被惩处而随之消弭。一般上,邪教组织犯罪中受害人人数众多,对公民信仰以及科学意识摧毁严重,甚至把“神”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因此,邪教组织虽然很少以实施暴力犯罪作为其直接的目标,然而邪教组织在特定领域所具有的社会危害,却并非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能企及。[3]同时,邪教组织是一个组织性强、分工精密、目的明确、行动诡密,既具有组织行为,也具有组织结构,还具有组织机构,完全符合刑法意义上的犯罪集团。
鉴此,依照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邪教犯罪的潜在巨大风险激活了政府的社会责任。[4]对于那些不可预知或难以控制的社会风险,应当在其未转化为现实的损害之前将其纳入法律的规制范围,于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而言,如果在刑法上继续放任邪教组织的成立与发展而不顾,当邪教组织所伴随的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危害时,刑法的介入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了。[5]“法轮功”的恶性发展,以及被取缔后,逐渐演变成为反对党和政府、背叛祖国和民族、不断造谣生事的反动政治组织,充分暴露了其邪教的罪恶本质,为人们认识邪教的长期性、特殊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标本,我国政府在当时反邪教立法尚未成熟的条件下,能当机立断,毅然而然地对其依法取缔,并以此为鉴,不断修订、完善我国反邪教立法,显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揭示、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敏感性、前瞻性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实践证明,我国反邪教法律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融合了法治和德治的治理方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管住管好邪教问题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德沃金(美)著:《没有上帝的宗教》,於中兴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6,P8-40
[2]朱建伟著:《中国古代邪教的形态与治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2,P3
[3]邵俊武:《邪教危害的特殊性及其法律治理》,陈少波主编:《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P357-359
[4]乌尔里希·贝克(德)著:《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2,P274
[5]聂立泽:《关于法律治理邪教问题的思考》,陈少波主编:《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P361-362


“全民反邪教,聚力护平安”反邪教短视频征集活动启事
在省委政法委的指导下,省反邪教协会、南方新闻网联合举办“全民反邪教,聚力护平安”反邪教短视频征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