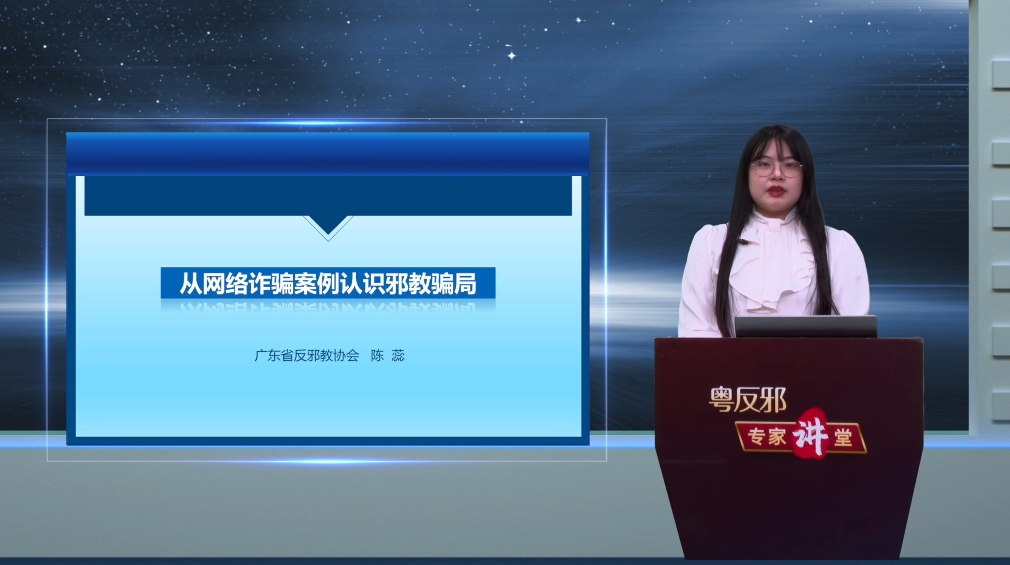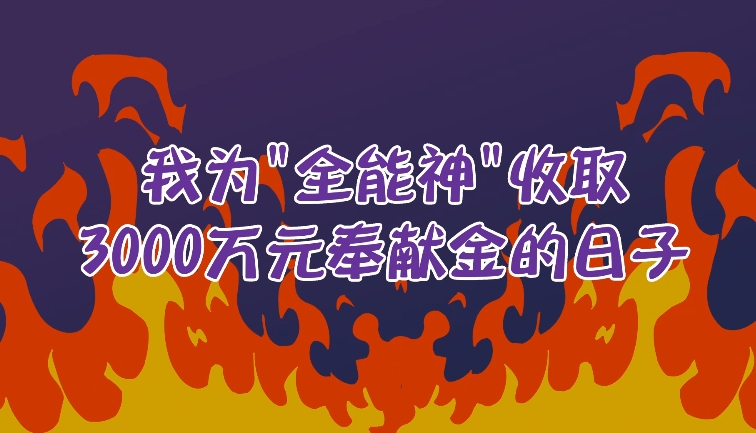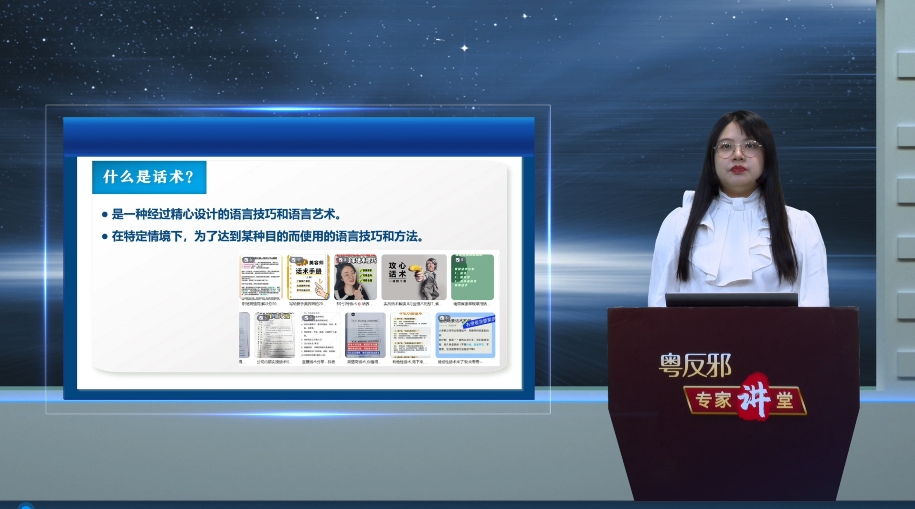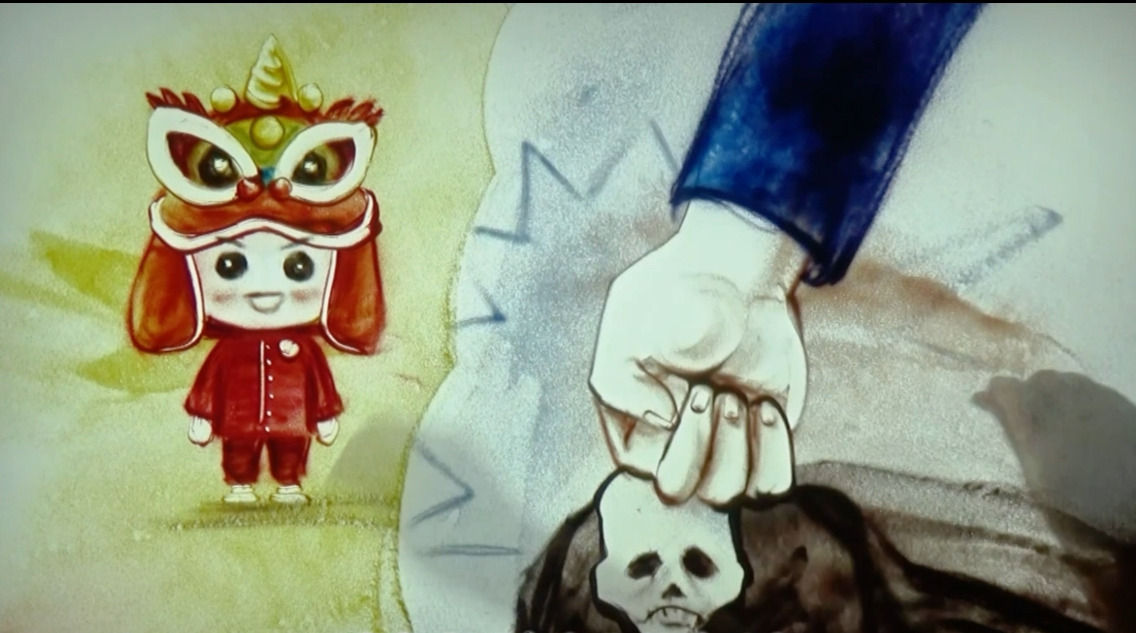彩虹过人被踢倒,为什么被骂的是内马尔?
——“指责受害人”现象及其心理成因分析
感冒发烧了,家人第一时间批评“早叫你多穿点衣服”;有人中了诈骗圈套,人们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贪心就不会受骗上当”;有人被抢劫、强奸,人们会想“大晚上还去那种地方”;绿茵场上,内马尔彩虹过人(一种用脚后跟把球挑起,从对方头顶越过的过人方式)被对手踢倒,网上一片声讨“动作花哨就是找踢”……
这样的情景很熟悉吧。不好的事情发生时,第一反应不是同情、安抚受害者,而是对其加以指责,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指责受害者”。

2021年11月,广州警方通报了一起因停车场纠纷而引发的故意伤害事件,保安捅伤车主,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新闻报道后,很多评论指向被害车主,“平时就嚣张”、“那是他活该”。为什么会这样?有学者认为,这与美国心理学家梅文·莱纳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有关。持这种信念的人相信世界是理想的、可控的,为了让自己保持内在认知和行为一致,他们会认为后果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但是,现实中持有“公正世界信念”的人数未必更多,而且,那些认为世界不公的人,似乎更可能产生指责受害者行为。“公正”多数时候更像是一种期望,是人们体会到世界“不公正”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保安刺死车主的案例中,大多数人理性上同意公正的处置是行凶者受到惩罚,但内心仍然惯性地指责受害者“罪有应得”,尤其那些认为自己与停车场管理员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
现在,让我们探讨其他心理成因。
1、反事实思维
加拿大心理学家齐瓦·孔达认为,人们常持有一种“反事实思维”,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受害者身上时,我们倾向于将其他事实看做是不可变的背景因素,因此我们尝试从改变受害者行为的角度做出解释,这可能是受害者常常因其不幸而受到谴责的原因。美国心理学家Kehneman和Tversky(1982)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描述了一种情境:琼斯先生平时都是沿市内道路驾车回家,一天下班后,为了欣赏海滨风光,他不走平时的路线,结果途中被一个醉酒司机酿成交通事故身亡。当要求被试想象琼斯先生的家人如何完成句子:“如果……该多好”时,被试的想象集中在:如果琼斯先生跟平时一样走另一条路,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反过来,当要求被试从肇事司机的角度想,大多数被试的反应是司机如果那天不喝酒,或者喝了酒不开车,车祸就不会发生了。这些研究结果暗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受害者受到的关注越多,人们越容易产生本来可以做点别的行为以避免悲剧发生的想法,从而产生对受害者的谴责行为。
2、事后诸葛亮
每天股市收盘,股评家们都能为当天涨跌找出一大堆理由。足球比赛输球之后,媒体、球迷满是这样的声音“这样排兵布阵怎么可能行”。金融危机发生后,总有人声称“早就知道这场危机不可避免”。当一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感知,深信自己早就知道会如此。我们重构过去的知识状态时,倾向于夸大对已发生事件结果的预知程度,而没有认识到,这些迹象是在我们了解事情的结局后才清晰起来,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称之为“知道”的错觉。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朋友离婚后,他们先前很多模棱两可的行为,都可以重新解释为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先兆,我们会回想起很多他们关系不合的细节,而对他们曾经恩爱的表现忽略不计。齐瓦·孔达认为,我们不能准确地重构过去的知识状态,这会导致我们严厉指责别人(或自己)的错误决定。错误一旦酿成,我们在事后会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从而把矛头指向受害者: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个荒谬的决定。
3、替代攻击与宣泄
人们时常有攻击的欲望和宣泄的需要。根据伦纳德·伯科威茨(Leonard Berkowitz)提出的修订后的挫折攻击假设,疼痛、高温以及心理不适等任何导致不愉快情绪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攻击性行为。随着文明发展、社会规范以及力量权衡等原因,人性中的攻击欲望常常受到压抑,不满情绪无处宣泄,这时就会产生替代攻击与宣泄的需要。替代性攻击(Dollard, 1939)是攻击行为的一种特定模式,指由于一些因素的抑制,受到挫折的个体无法直接对挫折来源发泄其情绪,转而对替代对象施以攻击。近年来,有些地方设立了“心理宣泄室”,进入里面可以随意攻击事先树立的假人、可以拿起物品乱砸一气等,就是为了迎合人们替代攻击与宣泄的心理需求(笔者注:但其效果值得商榷)。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会遇到蛮不讲理的人,有时会觉得自尊受损却没有机会还击,就会希望有人可以替自己出头,或者希望看到对方遭殃。替代性攻击目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替代攻击对象与期望攻击目标相似,在停车场保安与车主的案例中,网络上多数人不但指责受害者,还流传了很多“证据”,企图说明死者生前就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网友们常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指责受害人”的心理机制有其益处。反事实思维可以让我们从自身出发考虑如何避免类似的危险情境,世事难料,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就改变自己。替代攻击可以让我们宣泄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想法可以促进心理平衡,减少现实冲动。事后诸葛亮可以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帮助我们满怀信心地生活、工作。但是,指责受害人也可能蒙蔽我们对事实真相的认知和探求,一面之辞的指责还可能造成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造成受害者家属承受丧亲之痛还要被指责,被诈骗者不敢报警等后果。
“指责受害人”现象在邪教问题中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家人信了邪教,我们会指责他“脑子被驴踢了”。看到媒体关于邪教犯罪的报道,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骗局也有人信,邪教那些说辞简直荒谬透顶,怎么会有人深陷其中。这些指责不无道理,因为参加邪教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邪教受害者同时也是潜在或事实施害人,但是,不问缘由的指责也可能导致我们看待邪教问题简单化,阻碍我们对邪教本质、欺骗手法的深入探究,也不利于我们教育挽回被邪教蒙骗的家人。(篇幅所限,此方面内容另文展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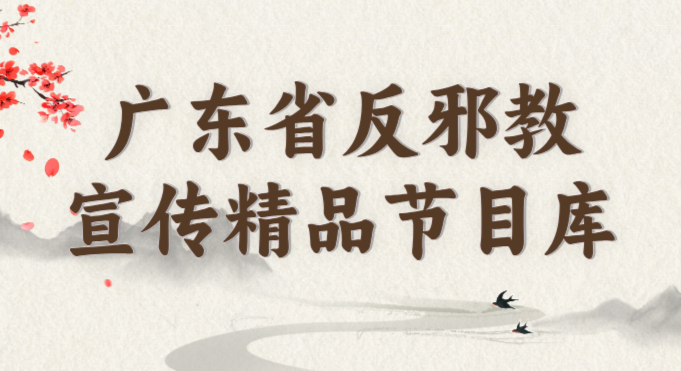
视听盛宴来袭!歌舞曲艺奏响反邪强音,“广东省反邪教宣传精品节目库”上线→
反邪文艺佳作轮番上阵,速来围观!